诗人南书堂:在秦岭深处写诗,在报纸背后看世界
■季风/文字整理 南书堂/供图
主持人:
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主编、作家)
对话嘉宾:
南书堂(《商洛日报》总编辑、著名诗人、作家)
嘉宾简介
南书堂,陕西商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从事媒体工作,断断续续写诗30多年,在《诗刊》《光明日报》《星星诗刊》《北京文学》等数十家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各种选本20多次,部分作品被译介到海外。著有诗集《采芝歌》《临河而居》《漫步者》《紫苜蓿》四部。曾获首届陕西省作家协会年度文学奖诗歌奖、《诗刊》《飞天》等全国诗歌大赛奖、《延河》《美文》杂志“最受读者欢迎作品奖”等奖项。
▲诗人南书堂在写作。

▲作家贾平凹为诗人南书堂题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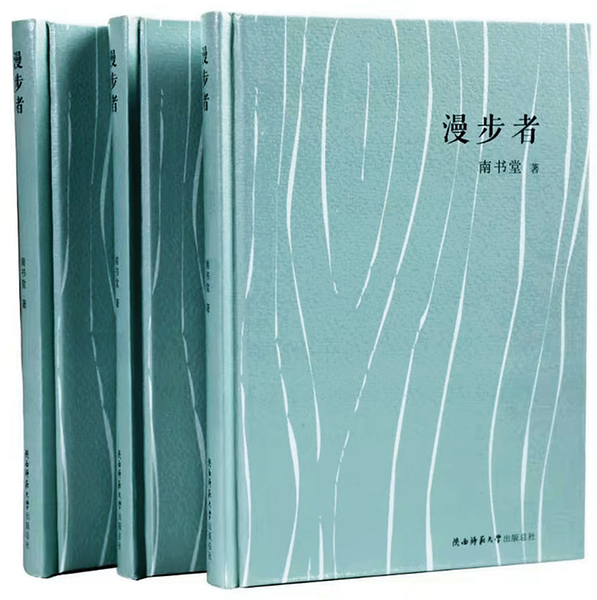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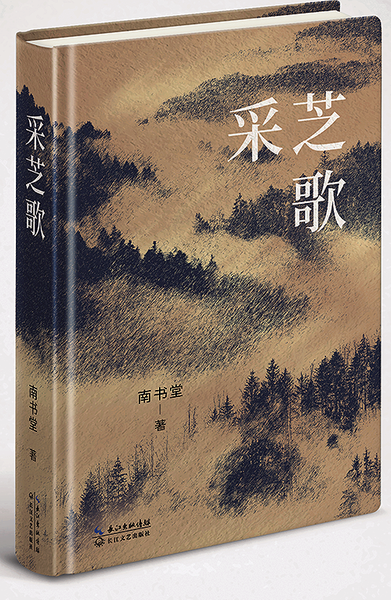
季风:“诗歌是我精神的采芝”—— 《采芝歌》书名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您将诗集命名为《采芝歌》,是否与“商山四皓”的典故有关?您如何看待诗歌与隐逸精神在当代的意义?
南书堂:很高兴以这样的方式与你相见,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采芝歌》是最近出版的我的第四部诗集,以其中一首诗的标题作了书名。书稿交出版社前,想过好几个名字,都被自己摇头否定了,正煎熬间,翻到《采芝歌》这首诗的那页,就有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觉得这个名字不算俗气,也不高深,还挺明快的,就在心里确定下来。远在上海的著名作家、诗人陈仓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一直关心着我这部诗集的出版,他看了书稿,说书名很好,与整部书很相配。征求其他朋友意见,也说好。有了朋友们的肯定,书最终这样命了名。
《采芝歌》这首诗本身就是写“商山四皓”的,我几乎不惜笔墨地对他们倾注了我诗歌中少有的饱满的赞颂之情,这不仅缘于他们隐逸在我所居的大秦岭、我的商山的那份亲近感,更缘于他们如此淡泊功名让我对他们生出的那份敬仰感。从古到今,人们都嘴上说着淡泊名利,但有多少人能像他们真正做到了呢?当高雅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也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时,“商山四皓”的隐逸精神也许能够缓冲诗人和诗歌的堕落。最起码,我想为自己筑起一道“防火墙”。
在当代,诗歌的隐逸绝不是诗歌的逃避,而诗人应像“商山四皓”采芝一样,以语言的纯净和精神的纯真,来书写世界、生活和生命的本真。
季风:“商洛是我的根,也是我的镜” —— 作为商洛诗人,地域文化如何滋养您的创作?
您的诗中频繁出现秦岭、丹江、商山等意象,它们对您而言是地理标志,还是精神符号?
南书堂:生于商洛,长于商洛,商洛是我的根、我的魂。无疑,商洛这块土地及其他的气象风物,成就了我的写作、我的诗歌。秦岭、丹江、商山,都是我家乡的大事物,它们默然耸立或喧嚣奔流,为我勾勒了一处庸常而充实的生活地理,一处高贵而虚幻的精神地理。我在这样的地理上忙碌地奔走着,放纵地闲适着,长久地思索着,无端地苦闷着,幸福着、感恩着、梦想着、抒写着……偶尔也因公因私而东西南北地出去走走,也被异地的美景所迷恋,为朋友的热情所感动。但不几天,就会心烦意乱起来,急切盼望回到自己惯常的山水相拥的环境里。遂想:人和草木一样,都是有根的……因此,我的情感,我的笔端,总自觉不自觉地滑向山水氤氲的气象,人们命运的起落,以及历史尚存的余温。我一直试图多角度呈现秦岭与丹江的容姿,发掘它们蕴藏的真谛,追问它们无解的命题,以期我的诗行能够挺立着秦岭的巍然,逶迤着丹江的隽永,弥漫着这方水土之上无处不在的灵性。
季风:“在报社看现实,在诗中见灵魂” —— 媒体人与诗人的身份如何共存?
作为一家地方党报总编辑,您如何处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诗歌创作的“主观性”之间的张力?
南书堂:其实,新闻和诗歌都要面对现实、反映现实,在“看现实”和“见灵魂”之间,二者并不完全冲撞和矛盾,都要直抵真相。所以,媒体人和诗人也不相互冲撞和矛盾,都是时代的叙述者和记录者。许多媒体人也是诗人,就像任何行业的从业者也可以成为诗人一样。我们报社就有好几位同志,不光是好记者、好编辑,还是好诗人、好作家。
新闻报道强调的是客观性,但采访到的那些大量客观真实的场景和细节,在作为新闻写作素材的同时,也会成为诗歌和其他文学体裁写作的素材,或者成为激发文学写作冲动与灵感的一种微妙的力量。也就是说,面对某一个事件,它本身的“客观性”是唯一的,但写作者的感知和联想,即“主观性”,可能又是多维的。这么多年,我在采访、写作和审理新闻稿件过程中,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启示或感悟,闲余时间,把它们写出来,其中一些感人至深的细节,被我写在新闻作品里,也写在了诗里。可以说,对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深度介入,客观上既拓宽了我的文学视野,又推动了我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实践,使我的作品有了坚实的根基。
季风:“诗可以观世,也可以‘救心’” —— 您如何看待诗歌的社会功能?
在您看来,诗歌在当今时代还能否承担启蒙、慰藉甚至批判的使命?
南书堂: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古往今来,诗歌的启蒙、慰藉、批判诸多社会功能,始终存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诗歌还以其自身短平快的特点,充当着文学反映生活和传递大众情感的先锋。
我并不担心诗歌的前景,被时代气象反复碰撞和感染的诗人们,不会堕落,诗歌不会堕落。诗歌的完全工具化和完全无用论,甚至极端的消亡说,都是不可能的。日月交替,斗转星移,但许多东西是永远不变的,人间依然有可抒发的美好情感,万物依然有可探究的秘密,世界依然有爱的温暖。
季风:“古典与现代之间,我选择散步” —— 您的诗中有浓厚的古典意境,也有现代性思考,您如何融合二者?在继承古典诗歌的传统中,又如何回应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南书堂:多年里,由于工作原因,闲暇时间总是碎片式的,我也适应这些碎片,养成了散步的习惯。散步的时候,我像浸淫在丹江与秦岭磅礴而鲜活的现代气象里,又像徜徉于它们无处不在的古老意象里,心绪穿越时空、穿越古今,我如同一个与历史和现实同时对话的人。我有一部诗集就叫《漫步者》,新诗集《采芝歌》也是我肌体与精神漫步的产物。
一些诗家和评家,比如叶延滨、胡弦、臧棣、张清华,他们都认为我的诗歌有着浓厚的古典意味,是我诗歌的一个明显特征。我不否认这一特征,也非有意在诗中强化这一特征,诗家们说这是我的一种文化自觉,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熏陶和潜移默化在起作用吧。我只是固执地认为,诗人应承袭而不是彻底抛弃诗歌传统,在弘扬诗歌传统特别是古典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去实现对传统的超越。我更看重诗歌的现代性,我把承继并试图超越传统当作本质上的现代性追求。
当今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情感因子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和各种新思维、新情绪,纷纷闯进我们的书写视野。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景象以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焦影像已不复再现,取而代之的是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农民就地转产转业和进城务工等新景观,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所思所想也与以前有了很大变化,那种在好长时间里被定格化的田园牧歌或者哀叹悲愁,已不是乡土上的症候。而城市随着环境品位的提升、流动人口的增加、不同文化的交融,曾经被视作一个自私与冷漠的代名词的生存时空,已有了越来越多的包容与温情的质感。再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自然界许多秘密被揭开,人们从自然那里得到的物质馈赠和心灵慰藉,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类修正精神缺失的要件。
如果诗人们对之视而不见,那么我们的诗歌写作就会陷入惰性经验的深渊,就背弃了对诗歌最突出的品质——现代性的秉持和追求。事实上,任何时代的诗歌,都不可能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不可能不体现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范,《诗经》如此,诗人屈原的诗歌如此,李白杜甫的诗歌亦如此。至于多大程度上呈现了现代性,关键在于诗人的能力。因此,诗人应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感应认知这个时代,应客观准确而不是主观臆想地把握这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以更博大的情怀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业已习惯的个体私密经验言说与这个时代命运、情感的揭示对接起来,使其相得益彰;以更宽广的视野和途径从这个时代的肌体中汲取养分,让诗歌的思想根系更加发达、枝叶更加繁茂、茎秆更加挺拔。
季风:“写诗是孤独的事,但读诗不是” —— 您希望读者从您的诗中获得什么?
您是否在意读者的解读?有没有一首诗是您特别希望被读者真正理解的?
南书堂:写诗时,一个人面对的是苍茫的世界、纷繁的思绪,一张白纸或一面蓝屏的空旷,但当一首诗被写出了,它给诗人带来的,又是抹去孤独的心灵慰藉,它在刊物或网络得以发表,就是诗人与读者对话交流的开始。这种对话交流不一定顺畅,可能无法达成那种灵魂交流的默契。因为落在纸上的文字,永远大于诗人最初的想法,自然而然,它也就有了不同解读。诗歌永恒的魅力,就在于这里。
季风:“语言是牢笼,也是翅膀” —— 您在诗歌语言上有什么样的追求?
您的语言简洁而富有意象,是否刻意避免过于华丽的修辞?您如何看待“白话诗”与“古典诗”的语言差异?
南书堂:写得久了,想法和顾忌也多了,就不得不讲究起来,像穿衣要照照镜子,看看得体不得体,穿哪样衣服更适合自己。我并不反对诗歌的华丽,也写过一些类似的诗,但我反对过度的炫技式的华丽,我以为它是对诗歌的放纵,是没有节制的奢侈,是本末倒置,是对诗歌的伤害。诗歌不像其他文学作品,体量大,情节复杂,可以藏纳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读者也不在乎这点瑕疵。而诗歌多一个字都显蹩脚,都像污点,更不用说多余的句子。在诗歌练习中,我一直做着减法,表达的减法、文字的减法,想尽量做到简洁,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因为在我看来,简洁不是干瘪,语言精准而感情丰沛,才是我心中诗歌的品相。做到这点很不容易。
季风:“诗人不是职业,是一种状态” —— 您如何看待“诗人”这个身份?
您是否认为诗人应该介入社会?还是更应保持一种疏离的姿态?
南书堂:我既看重“诗人”这个身份,又轻视它。看重它,并非欲从中获取什么,而是时时提醒自己,要对世界始终保持一种好奇之感,对熟悉事物保持一种发现之心。轻视它,甚或刻意掩藏它,是为了最大程度保持不受身份干扰的自我,远离那些热热闹闹的“诗歌事件”。
我很难想象一个躲在“象牙塔”不闻世间风雨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写出什么样的诗歌。归隐辋川的王维,诗歌里也有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何况处在当下信息时代的诗人?关注社会、热爱生活、拥抱生活,又有自己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诗歌才会拥抱你、热爱你。
季风:“未来的诗,还在秦岭深处生长” —— 您对未来的创作有何计划?
是否继续以商洛为背景写作?有没有尝试其他文体或题材的打算?
南书堂:非常喜欢你为我量身打造的这句话:未来的诗,还在秦岭深处生长。
我的创作,没有太明确的计划,但写商洛写家乡,肯定得继续,这是不二的选择;用诗歌把秦岭写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树立起自己诗歌的“秦岭”,也是努力方向,是必修课;多出去走走看看,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写点同家乡故土感受不一样的诗,让自己的人生见识和诗歌视野再丰富一些;尝试着写些长诗,弥补一下只写短诗的缺憾;写诗几十年,得寻求有大的突破、有新的气象,得给自己提一个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自加压力、自设难度,对自己对诗歌有个交待。
这些年,写诗之外也写了一些散文作品,有了一本书的体量和规模,写着写着,被那种舒展自如、尽情尽兴的感觉所陶醉,发现自己越来越爱散文了,那就让我像对待诗歌一样,倾心写出更多自己满意、读者喜爱的散文作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