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陈仓:人只有装在瓶子里,才会风平浪静
2025年07月24日
字数:5801
■季风/文字整理 陈仓/供图

主持人: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主编、作家)
对话嘉宾:陈仓(著名作家、诗人)

嘉宾简介
陈仓,“70后”诗人、小说家。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出版“进城系列”小说集《父亲进城》《小猪进城》等八卷,长篇小说《后土寺》《止痛药》《浮生》,长篇散文《预言家》《动物忧伤》,散文集《月光不是光》《丹凤》,长诗《醒神》《天鹅颂》,小说集《地下三尺》《再见白素贞》《从前有座庙》等。
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柳青文学奖、第五届大家文学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九届中国长诗奖等,中长篇小说多次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年度好小说(排行榜)。作品先后四次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主持中国文化艺术大家“系列访谈”栏目,已经推出作家、戏剧家、艺术家等200余人,主编《文化酵母》《光的方向》等“对话百家”系列丛书六卷。

作家陈仓与他的父亲在老家屋前。

作家陈仓在鲁迅文学奖颁奖会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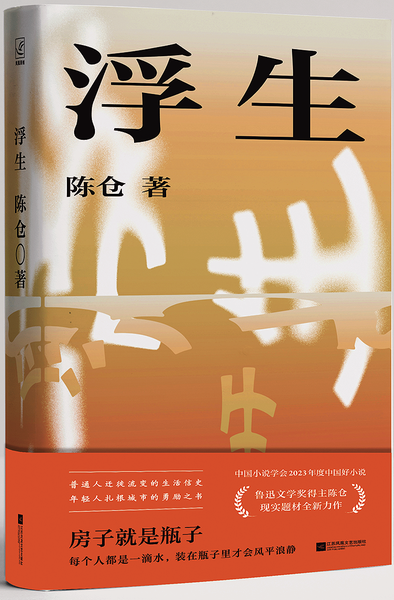
陈仓作品《浮生》。
编者按
2013年起,以“进城系列”作品切入文坛的陈仓,这么多年仍然走在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城市二元循环的道路上。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浮生》,继续保持着和时代贴心贴肉的风格,以充满诗意的笔调和浓郁的都市生活气息,描写了一对小夫妻在城市买房安家的故事。反映了大移民时代年青一代的痛与爱、正义与良知,以及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小说一经推出,立即引起了各类人群的强烈共鸣,将他的创作从接地气、感人心、通人性的路径,向着安妥灵魂、叩问现实的新高度不断提升。
季风:陈仓先生好,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您还在老家商洛某县当干部,现在在上海安家,离故乡是越来越远了。您远离陕西似乎是为了诗与远方,请您谈谈当初离开陕西的大致经历。
陈仓:非常不好意思,我们见过面吗?我对不上号了,只是隐约觉得似曾相识。这可能就是网络社会的特点,人和人之间的相识,不再是以具体形象来确定的,而是以一种情绪一种感觉一种精神来确定的。这就像西安下了一场雪,对身在其中的你而言,雪就是雪,可以堆成雪人,可以融化成水。上海是很少下雪的,所以对我而言,雪是一张照片一种颜色,甚至就是一个词语而已。
有一年腊月,我到上海玩,所住的酒店在静安区康定路,背后是一片石库门老房子。我那时候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城市,首先买一张地图,然后再买几份当地的报纸。有一天早晨,看到有一家报社也在康定路,而且就在酒店的隔壁。我就拨打了新闻热线,说自己是媒体同行,想找他们的总编辑或者社长聊聊。电话很快转给了社长,社长是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尤其是这种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比较儒雅,有一种说法叫“老克勒”。所以,他答应接待我。不过,他说只有十分钟时间,因为马上有会要开。
我来到位于21层的报社,和社长聊了聊,没有想到的是,一口气聊了两个小时。社长还打电话叫来了总编辑,请我在报社食堂的小包厢里吃了午饭。这么一聊,社长当即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团队,我也当即做了一个决定,准备独自闯荡上海滩。后来,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这家报社?我给出的说法是,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前,可以看到不远处的玉佛寺。其实,真实原因是,那时候年轻,内心充满着一股热情,怀抱着诗和远方的理想追求。
季风:作家贾平凹先生是您的乡党,你们应该关系更近些,能不能讲讲你们之间的来往?
陈仓:我和贾平凹老师都是丹凤县人,但是贾老师家的棣花位于县城以西30里,在丹江河畔,属于川道,说的是秦地方言,唱的也是秦腔。而我家的塔尔坪在县城东北80里的大山里,我的话和贾老师的话差别很大,不像河南话,也不像湖北话,发音上有点江南的腔调,最近去过一次安徽安庆,听了《牛郎织女》《天仙配》,我的方言和生活习惯和安庆人一模一样,比如把“吃”念成“气”,把睡觉叫“困醒”,把牛角念成“牛个”。我们从小也不听秦腔,而是听豫剧和黄梅戏,收听的也是河南、湖北的天气预报。
其实,我和贾老师认识很晚,那是2015年3月,红旗出版社给我一次性出了八本书,叫“陈仓进城系列”,《华商报》搞了一次研讨会,并出面邀请了贾老师。正是那次研讨会,我第一次见到贾老师。在那次研讨会上,贾老师作了非常认真的发言,最后整理出来有4000多字,他当时对我的评价是:“陈仓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小说有一种清新,这样一种清新,在文坛上刮起的风,像陕西老家的山风,你说硬它也硬,你说柔它也柔,反正是多种味气、多种味道都在里边。”
贾老师的前半句,当然是对我的鼓励,我很清楚自己的斤两。从此开始,我们之间才有了联系,而且联系非常少,见面就更少了。原因是,贾老师特别忙,我没有必要老是打扰他。而且文学创作是很个人化的事业,也是一份孤独的事业,别人只能鼓励你,当然善意的批评也是一种鼓励,所以一切都得靠自己去完成。
更何况,文人和文人之间,最美好的交往方式,就是在文字里见。贾老师的书,他每出一本,我就读一本。我以为,他太忙了,根本不读我的书,但是有一次在一起开会,他对我说,他读过我新出的小说集《地下三尺》和我的长诗《醒神》,觉得写得特别好,而且和其他人的作品进行了对比。他的话不像表扬那么简单,而是有些“知己”的意味。我当时的心情,有点春风拂柳的感觉。柳树被春风一吹,不仅要摇晃一下,还有一种绿的冲动。
我想说的意思是,贾老师这些大家前辈,包括我们商洛老乡陈彦,他们都是参天大树,我们是大树下的小草。大树对于小草的意义是作为灯塔去仰望,而非像叽叽喳喳的麻雀去攀附。
季风:贾平凹先生评价您是“把故乡背在脊背上到处跑”的作家,作品《浮生》依然关注进城人员的生命状态。您是怎么理解大移民时代关于“故乡”这个话题的?
陈仓:“故乡”一词的定义是:“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中国古代对故乡有许多雅称,有桑梓、家山、故国等。但是,结合我个人的经历,我觉得“故乡”的“故”有“故去”的意思,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死亡”。
我的故乡在商洛市丹凤县塔尔坪,我家有三间大瓦房,其中主卧里有一张床,床上铺着麦草。我是在那张床上出生的,是在那张床上长大的。我的母亲、哥哥、后妈、父亲,他们四个人,先后在那张床上睡过,最后都是在那张床上去世的。我的父亲,虽然是在医院掉气的,但是在家里的那张床上入殓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灵魂是从我们家的房子里消逝的,而且是灵魂“出煞”“回阳”的地方。我觉得,有灵魂出没的地方,才具有故乡的内涵和气息。
现在是一个大迁徙的时代,也可以称之为漂泊的时代。开始有一位老师给《浮生》起了个名字就叫《漂泊时代》,感觉特别贴切。随着不断的迁徙,我们似乎没有了故乡,其实不然,故乡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像一件行李一样,被我们随身携带着而已。就是在那次研讨会上,贾平凹老师看到我漂泊的经历和我老家的现状,才说出了那句话——陈仓是把故乡背在脊背上到处跑的人。
他的这句话特别形象,道出了我的生存状态。因为我离开故乡以后,上过北京,下过广州,如今长住上海,可以说是东南西北都跑遍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脚步比别人疲惫,我的风尘比别人大,我流浪的地方比别人多,我的行李比别人重。所以,我的故乡就比别人重。别人可以把故乡提在手中,可以把故乡揣在怀里,但是我的故乡太重,我只能像搬运工人一样,把麻袋扛在肩膀上,弯着腰,弓着背,低着头,迈着沉重的脚步。
季风:陕西地分南北,南部是秦巴山脉,北部是黄土高原,中间是关中平原,地域不同让人物性格也迥异。商洛的人民心性善良宽厚,有吃苦耐劳的品质。您如何看待故乡的风土、人物,包括地理气象和山山水水?
陈仓:商洛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作家群,很多朋友给出的答案是文化底蕴深厚。我觉得真正原因可能是商洛处在南北分界线上,秦文化和楚文化在此碰撞,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文明在此交融,最后形成了一种灵性和厚重兼得的独特文化。
商洛人最大的特点是特别善良,我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找出了善良的基因。我们从小受到的文化教育都是从老戏中来的,我们商洛人唱秦腔、豫剧,也唱黄梅戏,大部分都是讲如何积德行善的,比如秦腔《铡美案》里千里寻夫却毫无怨恨的秦香莲,豫剧《卷席筒》里替嫂嫂顶罪的苍娃,黄梅戏《天仙配》里卖身葬父的董永。
这种纯朴善良的民风就是这样形成的,让我念念不忘的两个故事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母亲断气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吃麻花,父亲和姐姐跑遍了整个村子,借来半桶油和一升面粉,好不容易炸好了麻花,母亲却已经断气了,把人间的美味留给了我;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哥哥带着我去河南淘金,中途发生了一次事故,哥哥救了我,却献出了他十九岁的命……正是我的父老乡亲,用他们纯朴的爱和善良,为我的人生铺就了温暖的底色,教会了我如何善待世界,如何去热爱土地和生活。
季风:常有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您觉得善意对于文学作品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陈仓:善意是人最优秀的品质,也是人的最高境界,更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所在。《浮生》也是靠着善意而活着的,陈小元和胥小曼,小叶和柳红,这些人物都是充满善意的,只不过他们表达善意的方式不同而已。所以,这部小说运气特别好,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重点扶持项目,发表在《十月·长篇小说》2023年第3期,《长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纷纷转载,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年度中国好小说,长篇小说共评出了5部,其中3部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写的。
人的生命靠氧气、水分和食物来维持,那么文学作品的生命力靠什么来维持呢?对我而言,我觉得需要靠着一种善意,来感染人、鼓舞人和软化人,从而把路走得更宽更高更远,更加富有光芒的色调。
季风:您先是一位诗人,后来成了小说家,你把这种转化说成“天意”,你能不能解读一下这句话?您的长篇作品《浮生》也是所谓的天意产物吗?
陈仓:我不是迷信,我只是想说,文学对我来说是上天交给我的事业。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自己修行得来的,我现在能够成为一个文人,很有可能是由一个个文字修行过来的。白素贞经过一千七百年的努力,由一条蛇修行成了一个大美女,我这个歪瓜裂枣的男人,由一个个文字修行过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起码,它们修行成了我的眼睛、耳朵、澎湃的血液和跳动的心脏。
我的经历可以证明我的话。我是放牛娃出身,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文盲,小时候除了几本连环画,没有看过几本课外书,不知道文学为何物,不知道作家诗人为何物,我和文学之间是一片空白。但是,非常奇怪,中学毕业的那年暑假,就在一片空白的状态下,我一边放牛一边开始写“诗”。我记得非常清楚,在一个没有用完的作业本上,每天都会写几句,写的比较多的是去世的母亲。大意是,妈呀,你这么漂亮,人这么好,应该已经成了神仙。如果你成了神仙,就赶紧来救救我。我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夸张,我就是这样开始的。你说说,如果不是前世的修行,怎么可能走上写作的道路呢?
大概到了2011年吧,我把父亲从陕西农村接到城里一起过春节,带他坐飞机、逛大雁塔、登西安城楼,到上海看海、洗桑拿、吃火锅……这些都是父亲的第一次,所以发生了许多令人心酸的事情,每天回家等父亲入睡以后,我就把父亲进城发生的事情,以日记的形式记了下来。后来,我打印了一份寄给了《花城》,2012年年底,我接到样刊打开一看,竟然发在了中篇小说头条。蝴蝶效应就这么产生了,《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纷纷转载了。这么一篇非常写实的散文,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变成了我的小说成名作。我就趁热打铁,不过一年时间,我就多了一个身份——小说家。
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浮生》也差不多,我并没有像许多小说家那样,拉开架势刻意去写。好像同样是天意,我认识的一位诗人朋友,他打电话向我求救,说他们花费几千万元买下来的房子,竟然有质量问题,希望媒体能够关注一下。朋友给我提供的各种资料,整整装了一大纸箱,足足三十多斤。我翻了翻资料,非常气愤,毕竟自己是记者出身,是有正义感的,于是就派了两位记者,去现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再后来,朋友发现我小说写得风生水起,希望我换一种身份,以小说家的名义,把他们的遭遇写成小说。我实在太同情他们了,他们花费一生的心血,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买下的房子竟然是那个样子。同时,我目睹了上海房价,从七八千块钱一平方米,涨到了十几万元、几十万元一平方米,许许多多年轻人为了买房子安家,可以说是被压得喘不过气了。
所以,有一年春节,我就动了笔,没有拉提纲,没有收集什么资料,完全是一口气写下来的。胥小曼、柳红、兰惠、胥海清,这些善良、漂亮、乐观的女人;陈小元、小叶,这些充满正义感的进城人员,都是自愿而自然地走到了我的笔下,充当了我的主人公。
季风:《浮生》主要是写房子的,房子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移民时代人们的精神家园。我觉得您的房子不仅仅是房子,似乎还有很强的象征意味?
陈仓:除了房子,还有酒瓶、青蛙、水坑等,这些意象确实有着象征意味。比如《浮生》里,有一个像巫师一样的流浪汉,喜欢收集空瓶子,而且特别喜欢敲打空瓶子。他捡到了两个瓷器一样的空瓶子,特别漂亮,舍不得扔,就送给了陈小元。陈小元把两个空瓶子摆在家里,当成了一种装饰。其实,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大概十几年前,我捡到一个空酒瓶子,准备摔碎听一下破裂的响声。但是朋友告诉我,这种酒很贵,一瓶好几千块,买都买不到,和市场上的房子特别像。我很吃惊,就陆续收集了几个这样的空瓶子,带回家放在窗台上,有事没事敲那么几下,像是古代人敲着编钟一样。空瓶子对我们这些漂泊的人来说是一种乐器,也可以说是替动荡的生活发声。所以空瓶子的身影在《浮生》里贯穿始终,而且有一段话:房子就像瓶子,我们每个人就是一滴水,水装在瓶子里才会风平浪静。
还有青蛙和水坑,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那是我在上海买房子以后。我买的是期房,因为特别期待,就经常跑到工地,看看房子盖得怎么样了。当时,工地挖了好多坑,坑里积了好多水,我就特别好奇,坑是新挖的,怎么会有蝌蚪在里边游动。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蝌蚪长大了,我竟然听到青蛙呱呱的叫声从这些水坑里传来。但是,等到房子盖好了,我搬进新家以后,我专门找过那些水坑,可惜全被填平了,当然再也没有听到青蛙的叫声了。我就想,青蛙都去哪里了?青蛙会不会被埋藏在我们的小区里?青蛙的处境和我特别相似,我们为了安家,正把自己的青春一点点埋在这片土地里。
大移民时代有一个特点,每个人都是漂浮不定的,我形容这样的人生像一个塑料袋,飘又飘不上去,落又落不下来,有一种特别无力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精神都是动荡的,特别需要类似于瓶子一样的容器,也特别怀念象征田园和家园的蛙声。

主持人: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主编、作家)
对话嘉宾:陈仓(著名作家、诗人)

嘉宾简介
陈仓,“70后”诗人、小说家。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出版“进城系列”小说集《父亲进城》《小猪进城》等八卷,长篇小说《后土寺》《止痛药》《浮生》,长篇散文《预言家》《动物忧伤》,散文集《月光不是光》《丹凤》,长诗《醒神》《天鹅颂》,小说集《地下三尺》《再见白素贞》《从前有座庙》等。
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柳青文学奖、第五届大家文学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九届中国长诗奖等,中长篇小说多次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年度好小说(排行榜)。作品先后四次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主持中国文化艺术大家“系列访谈”栏目,已经推出作家、戏剧家、艺术家等200余人,主编《文化酵母》《光的方向》等“对话百家”系列丛书六卷。

作家陈仓与他的父亲在老家屋前。

作家陈仓在鲁迅文学奖颁奖会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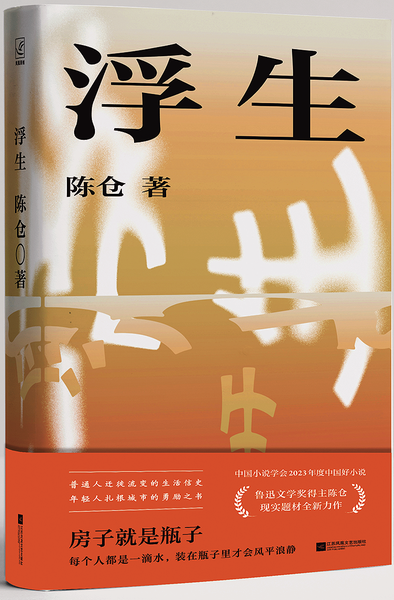
陈仓作品《浮生》。
编者按
2013年起,以“进城系列”作品切入文坛的陈仓,这么多年仍然走在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城市二元循环的道路上。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浮生》,继续保持着和时代贴心贴肉的风格,以充满诗意的笔调和浓郁的都市生活气息,描写了一对小夫妻在城市买房安家的故事。反映了大移民时代年青一代的痛与爱、正义与良知,以及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小说一经推出,立即引起了各类人群的强烈共鸣,将他的创作从接地气、感人心、通人性的路径,向着安妥灵魂、叩问现实的新高度不断提升。
季风:陈仓先生好,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您还在老家商洛某县当干部,现在在上海安家,离故乡是越来越远了。您远离陕西似乎是为了诗与远方,请您谈谈当初离开陕西的大致经历。
陈仓:非常不好意思,我们见过面吗?我对不上号了,只是隐约觉得似曾相识。这可能就是网络社会的特点,人和人之间的相识,不再是以具体形象来确定的,而是以一种情绪一种感觉一种精神来确定的。这就像西安下了一场雪,对身在其中的你而言,雪就是雪,可以堆成雪人,可以融化成水。上海是很少下雪的,所以对我而言,雪是一张照片一种颜色,甚至就是一个词语而已。
有一年腊月,我到上海玩,所住的酒店在静安区康定路,背后是一片石库门老房子。我那时候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城市,首先买一张地图,然后再买几份当地的报纸。有一天早晨,看到有一家报社也在康定路,而且就在酒店的隔壁。我就拨打了新闻热线,说自己是媒体同行,想找他们的总编辑或者社长聊聊。电话很快转给了社长,社长是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尤其是这种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比较儒雅,有一种说法叫“老克勒”。所以,他答应接待我。不过,他说只有十分钟时间,因为马上有会要开。
我来到位于21层的报社,和社长聊了聊,没有想到的是,一口气聊了两个小时。社长还打电话叫来了总编辑,请我在报社食堂的小包厢里吃了午饭。这么一聊,社长当即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团队,我也当即做了一个决定,准备独自闯荡上海滩。后来,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这家报社?我给出的说法是,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前,可以看到不远处的玉佛寺。其实,真实原因是,那时候年轻,内心充满着一股热情,怀抱着诗和远方的理想追求。
季风:作家贾平凹先生是您的乡党,你们应该关系更近些,能不能讲讲你们之间的来往?
陈仓:我和贾平凹老师都是丹凤县人,但是贾老师家的棣花位于县城以西30里,在丹江河畔,属于川道,说的是秦地方言,唱的也是秦腔。而我家的塔尔坪在县城东北80里的大山里,我的话和贾老师的话差别很大,不像河南话,也不像湖北话,发音上有点江南的腔调,最近去过一次安徽安庆,听了《牛郎织女》《天仙配》,我的方言和生活习惯和安庆人一模一样,比如把“吃”念成“气”,把睡觉叫“困醒”,把牛角念成“牛个”。我们从小也不听秦腔,而是听豫剧和黄梅戏,收听的也是河南、湖北的天气预报。
其实,我和贾老师认识很晚,那是2015年3月,红旗出版社给我一次性出了八本书,叫“陈仓进城系列”,《华商报》搞了一次研讨会,并出面邀请了贾老师。正是那次研讨会,我第一次见到贾老师。在那次研讨会上,贾老师作了非常认真的发言,最后整理出来有4000多字,他当时对我的评价是:“陈仓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小说有一种清新,这样一种清新,在文坛上刮起的风,像陕西老家的山风,你说硬它也硬,你说柔它也柔,反正是多种味气、多种味道都在里边。”
贾老师的前半句,当然是对我的鼓励,我很清楚自己的斤两。从此开始,我们之间才有了联系,而且联系非常少,见面就更少了。原因是,贾老师特别忙,我没有必要老是打扰他。而且文学创作是很个人化的事业,也是一份孤独的事业,别人只能鼓励你,当然善意的批评也是一种鼓励,所以一切都得靠自己去完成。
更何况,文人和文人之间,最美好的交往方式,就是在文字里见。贾老师的书,他每出一本,我就读一本。我以为,他太忙了,根本不读我的书,但是有一次在一起开会,他对我说,他读过我新出的小说集《地下三尺》和我的长诗《醒神》,觉得写得特别好,而且和其他人的作品进行了对比。他的话不像表扬那么简单,而是有些“知己”的意味。我当时的心情,有点春风拂柳的感觉。柳树被春风一吹,不仅要摇晃一下,还有一种绿的冲动。
我想说的意思是,贾老师这些大家前辈,包括我们商洛老乡陈彦,他们都是参天大树,我们是大树下的小草。大树对于小草的意义是作为灯塔去仰望,而非像叽叽喳喳的麻雀去攀附。
季风:贾平凹先生评价您是“把故乡背在脊背上到处跑”的作家,作品《浮生》依然关注进城人员的生命状态。您是怎么理解大移民时代关于“故乡”这个话题的?
陈仓:“故乡”一词的定义是:“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中国古代对故乡有许多雅称,有桑梓、家山、故国等。但是,结合我个人的经历,我觉得“故乡”的“故”有“故去”的意思,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死亡”。
我的故乡在商洛市丹凤县塔尔坪,我家有三间大瓦房,其中主卧里有一张床,床上铺着麦草。我是在那张床上出生的,是在那张床上长大的。我的母亲、哥哥、后妈、父亲,他们四个人,先后在那张床上睡过,最后都是在那张床上去世的。我的父亲,虽然是在医院掉气的,但是在家里的那张床上入殓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灵魂是从我们家的房子里消逝的,而且是灵魂“出煞”“回阳”的地方。我觉得,有灵魂出没的地方,才具有故乡的内涵和气息。
现在是一个大迁徙的时代,也可以称之为漂泊的时代。开始有一位老师给《浮生》起了个名字就叫《漂泊时代》,感觉特别贴切。随着不断的迁徙,我们似乎没有了故乡,其实不然,故乡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像一件行李一样,被我们随身携带着而已。就是在那次研讨会上,贾平凹老师看到我漂泊的经历和我老家的现状,才说出了那句话——陈仓是把故乡背在脊背上到处跑的人。
他的这句话特别形象,道出了我的生存状态。因为我离开故乡以后,上过北京,下过广州,如今长住上海,可以说是东南西北都跑遍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脚步比别人疲惫,我的风尘比别人大,我流浪的地方比别人多,我的行李比别人重。所以,我的故乡就比别人重。别人可以把故乡提在手中,可以把故乡揣在怀里,但是我的故乡太重,我只能像搬运工人一样,把麻袋扛在肩膀上,弯着腰,弓着背,低着头,迈着沉重的脚步。
季风:陕西地分南北,南部是秦巴山脉,北部是黄土高原,中间是关中平原,地域不同让人物性格也迥异。商洛的人民心性善良宽厚,有吃苦耐劳的品质。您如何看待故乡的风土、人物,包括地理气象和山山水水?
陈仓:商洛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作家群,很多朋友给出的答案是文化底蕴深厚。我觉得真正原因可能是商洛处在南北分界线上,秦文化和楚文化在此碰撞,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文明在此交融,最后形成了一种灵性和厚重兼得的独特文化。
商洛人最大的特点是特别善良,我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找出了善良的基因。我们从小受到的文化教育都是从老戏中来的,我们商洛人唱秦腔、豫剧,也唱黄梅戏,大部分都是讲如何积德行善的,比如秦腔《铡美案》里千里寻夫却毫无怨恨的秦香莲,豫剧《卷席筒》里替嫂嫂顶罪的苍娃,黄梅戏《天仙配》里卖身葬父的董永。
这种纯朴善良的民风就是这样形成的,让我念念不忘的两个故事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母亲断气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吃麻花,父亲和姐姐跑遍了整个村子,借来半桶油和一升面粉,好不容易炸好了麻花,母亲却已经断气了,把人间的美味留给了我;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哥哥带着我去河南淘金,中途发生了一次事故,哥哥救了我,却献出了他十九岁的命……正是我的父老乡亲,用他们纯朴的爱和善良,为我的人生铺就了温暖的底色,教会了我如何善待世界,如何去热爱土地和生活。
季风:常有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您觉得善意对于文学作品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陈仓:善意是人最优秀的品质,也是人的最高境界,更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所在。《浮生》也是靠着善意而活着的,陈小元和胥小曼,小叶和柳红,这些人物都是充满善意的,只不过他们表达善意的方式不同而已。所以,这部小说运气特别好,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重点扶持项目,发表在《十月·长篇小说》2023年第3期,《长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纷纷转载,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年度中国好小说,长篇小说共评出了5部,其中3部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写的。
人的生命靠氧气、水分和食物来维持,那么文学作品的生命力靠什么来维持呢?对我而言,我觉得需要靠着一种善意,来感染人、鼓舞人和软化人,从而把路走得更宽更高更远,更加富有光芒的色调。
季风:您先是一位诗人,后来成了小说家,你把这种转化说成“天意”,你能不能解读一下这句话?您的长篇作品《浮生》也是所谓的天意产物吗?
陈仓:我不是迷信,我只是想说,文学对我来说是上天交给我的事业。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自己修行得来的,我现在能够成为一个文人,很有可能是由一个个文字修行过来的。白素贞经过一千七百年的努力,由一条蛇修行成了一个大美女,我这个歪瓜裂枣的男人,由一个个文字修行过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起码,它们修行成了我的眼睛、耳朵、澎湃的血液和跳动的心脏。
我的经历可以证明我的话。我是放牛娃出身,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文盲,小时候除了几本连环画,没有看过几本课外书,不知道文学为何物,不知道作家诗人为何物,我和文学之间是一片空白。但是,非常奇怪,中学毕业的那年暑假,就在一片空白的状态下,我一边放牛一边开始写“诗”。我记得非常清楚,在一个没有用完的作业本上,每天都会写几句,写的比较多的是去世的母亲。大意是,妈呀,你这么漂亮,人这么好,应该已经成了神仙。如果你成了神仙,就赶紧来救救我。我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夸张,我就是这样开始的。你说说,如果不是前世的修行,怎么可能走上写作的道路呢?
大概到了2011年吧,我把父亲从陕西农村接到城里一起过春节,带他坐飞机、逛大雁塔、登西安城楼,到上海看海、洗桑拿、吃火锅……这些都是父亲的第一次,所以发生了许多令人心酸的事情,每天回家等父亲入睡以后,我就把父亲进城发生的事情,以日记的形式记了下来。后来,我打印了一份寄给了《花城》,2012年年底,我接到样刊打开一看,竟然发在了中篇小说头条。蝴蝶效应就这么产生了,《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纷纷转载了。这么一篇非常写实的散文,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变成了我的小说成名作。我就趁热打铁,不过一年时间,我就多了一个身份——小说家。
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浮生》也差不多,我并没有像许多小说家那样,拉开架势刻意去写。好像同样是天意,我认识的一位诗人朋友,他打电话向我求救,说他们花费几千万元买下来的房子,竟然有质量问题,希望媒体能够关注一下。朋友给我提供的各种资料,整整装了一大纸箱,足足三十多斤。我翻了翻资料,非常气愤,毕竟自己是记者出身,是有正义感的,于是就派了两位记者,去现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再后来,朋友发现我小说写得风生水起,希望我换一种身份,以小说家的名义,把他们的遭遇写成小说。我实在太同情他们了,他们花费一生的心血,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买下的房子竟然是那个样子。同时,我目睹了上海房价,从七八千块钱一平方米,涨到了十几万元、几十万元一平方米,许许多多年轻人为了买房子安家,可以说是被压得喘不过气了。
所以,有一年春节,我就动了笔,没有拉提纲,没有收集什么资料,完全是一口气写下来的。胥小曼、柳红、兰惠、胥海清,这些善良、漂亮、乐观的女人;陈小元、小叶,这些充满正义感的进城人员,都是自愿而自然地走到了我的笔下,充当了我的主人公。
季风:《浮生》主要是写房子的,房子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移民时代人们的精神家园。我觉得您的房子不仅仅是房子,似乎还有很强的象征意味?
陈仓:除了房子,还有酒瓶、青蛙、水坑等,这些意象确实有着象征意味。比如《浮生》里,有一个像巫师一样的流浪汉,喜欢收集空瓶子,而且特别喜欢敲打空瓶子。他捡到了两个瓷器一样的空瓶子,特别漂亮,舍不得扔,就送给了陈小元。陈小元把两个空瓶子摆在家里,当成了一种装饰。其实,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大概十几年前,我捡到一个空酒瓶子,准备摔碎听一下破裂的响声。但是朋友告诉我,这种酒很贵,一瓶好几千块,买都买不到,和市场上的房子特别像。我很吃惊,就陆续收集了几个这样的空瓶子,带回家放在窗台上,有事没事敲那么几下,像是古代人敲着编钟一样。空瓶子对我们这些漂泊的人来说是一种乐器,也可以说是替动荡的生活发声。所以空瓶子的身影在《浮生》里贯穿始终,而且有一段话:房子就像瓶子,我们每个人就是一滴水,水装在瓶子里才会风平浪静。
还有青蛙和水坑,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那是我在上海买房子以后。我买的是期房,因为特别期待,就经常跑到工地,看看房子盖得怎么样了。当时,工地挖了好多坑,坑里积了好多水,我就特别好奇,坑是新挖的,怎么会有蝌蚪在里边游动。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蝌蚪长大了,我竟然听到青蛙呱呱的叫声从这些水坑里传来。但是,等到房子盖好了,我搬进新家以后,我专门找过那些水坑,可惜全被填平了,当然再也没有听到青蛙的叫声了。我就想,青蛙都去哪里了?青蛙会不会被埋藏在我们的小区里?青蛙的处境和我特别相似,我们为了安家,正把自己的青春一点点埋在这片土地里。
大移民时代有一个特点,每个人都是漂浮不定的,我形容这样的人生像一个塑料袋,飘又飘不上去,落又落不下来,有一种特别无力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精神都是动荡的,特别需要类似于瓶子一样的容器,也特别怀念象征田园和家园的蛙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