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说地图
2025年03月07日
字数:1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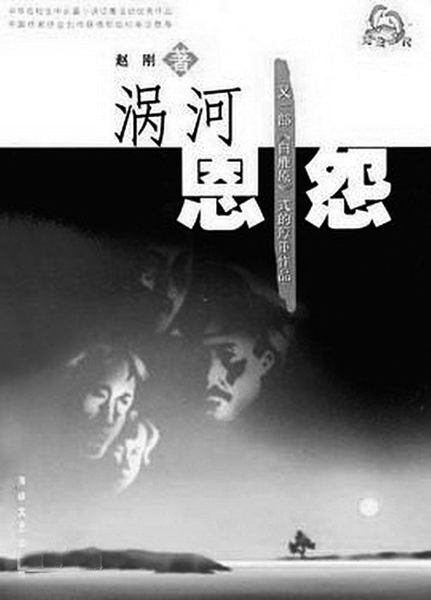
■赵刚
与大多数作家先诗歌、再散文、再小说的创作轨迹和先发表、再获奖的成长轨迹有所不同的是,我在文学园林最先收获的是小说,轨迹是先获奖、再发表。因此,我的文学地图从我的小说地图起笔。我的小说地图之起点站,大致从初中二年级暑假那次小说事件说起。
那是1989年暑假临近尾声的一个午后,无意中在邻居家的收音机里,听到省电台重播省军区与西安晚报社联合举办有奖征文的启事,我顿时心头一热,旋即又一紧。热的是,文学是我的挚爱,征文良机岂能错过?紧的是,截稿时间为次日,要想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有所斩获,谈何容易!惯常的诗歌、散文,显然难以承载我所要表达的主题,因此“突发奇想”,何不以小说试笔呢?经过整整一个下午的构思,决定以身为烈士遗孤的“我”,与在部队服役的父亲屈指可数的三次短聚入题,展现人民子弟兵“一家不圆万家圆,我为祖国守边关”的崇高境界。晚饭后正式动笔前,为了防止困倦袭扰,从不食辣的我,特意找来一根绿辣椒,决心用它提神醒脑。彻夜,我都沉浸在“烈士遗孤”与“英雄父亲”无限深情的《爸爸,请您收下》的激情创作中,早将那根虎视眈眈的绿辣椒忘到了九霄云外。
不久,省军区和西安晚报社的两名同志专程送来获奖通知书,代表组委会作出两点提议:一是欲把我的这篇军旅文学(没错,这是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听说“军旅文学”这个词)改编成电视剧,二是可以考虑特招我入伍。父亲代表我们全家,字斟句酌地阐述了两个观点:一是儿子年纪尚幼,知识有限,该读的书还是得读,该经历的事还是得经历,不宜拔苗助长,否则,于个人成长无益,于国家事业无益;二是好男儿志在四方,待条件成熟时,全家人会支持我参军报国。实践证明,父亲的顾虑不无道理,因为自从2年后即1991年冬入伍,至2001年秋,我在边防战士、军校学员、军事教员岗位摸爬滚打10载,却无一篇能拿得出手的小说(尽管此期间长篇小说《潇洒雨季》在期刊连载和由省电台连播),可见,父亲所言“该读的书还是得读,该经历的事还是得经历”讲得何其中肯,不仅是我矢志文学的航灯,亦是我人生成长的座右铭。
真正使我意识到自己具有小说写作天赋的机缘,是在2001年夏秋时节,不安分的创作冲动不失时机地跃入我的脑海,忠奸参半的蒋家“六虎”、恶贯满盈的匪首卢四、狡诈残暴的日寇龟泽高、除暴安良的蒋新贵、贤淑大义的李青云、足智多谋的葛中文以及义仆孙歪嘴、阿珍夫妇等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时常引得我在军政训练之余,将自己封闭在营区闷热难耐的仓库兼鸽子房里笔耕不辍。当我历时百日,为这部名为《涡河恩怨》的长篇小说画上句号的时候,适逢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与海峡文艺出版社联办的首届“海峡·冰心杯”全国中长篇小说征集出版活动启动,《涡河恩怨》从200余部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荣获优秀作品奖并正式出版的6部单行本之一。著名评论家施晓宇先生代表评委会,以《鲜活而凄美的乡村传奇》为题撰评,其中写道:“这部小说通过蒋氏家族祖孙三代的传奇经历,从清末民初一直写到二十一世纪,其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乃至悲喜交集、祸福相倚,反映了作者赵刚老到成熟的文字功底和对民俗风情的表现功力。单从小说的整体构思以及故事框架上看,不难让人联想到又一部《白鹿原》的问世。”或许,这正是《涡河恩怨》封面赫然标注“又一部《白鹿原》式的厚重作品”之故了。我一口气跑到北京最大的两家书店——王府井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把新上架的十几本书包圆,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在我看来,长篇小说写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若无鲜明主题、厚重构思作支撑,终究难有不俗表现。正是因为有过《涡河恩怨》的实践,我才对长篇小说写作敬若神明,决心扎扎实实完成一批中短篇练笔,以期为下一部长篇创作奠定基础。在中短篇小说创作实践过程中,“八水”这个虚拟的山城小县时常跳跃在我的心房,令我感到轻松、愉快,乃至于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是那样似曾相识而不可复制,真切朴实且可触可摸。我曾自问为什么会这样?旋即醒悟过来,西安是我的故乡,“八水绕长安”之胜境早在我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我笔下的“八水”山城,是这样拉开帷幕的——“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版图中心偏北某区域无限放大,一处像极了疖子的黄褐色‘斑块’上依稀可见‘八水’二字”(见中篇小说《八水故事》开篇语),它既含大关中,又纳东西府,还囊括古朴灵秀的陕南气象,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哩!于是,《黑头赵》《吴难事纪事》《赵小花的幸福生活》《戏比天大》《难念的经》等纷纷破土萌发,其中,《重返兴旺渠》被改编为电影、电视栏目剧及大型秦腔现代戏《兴旺渠风波》,公映(公演)后受到好评,剧本入选《2017全国优秀戏剧剧本专辑》,作为戏剧创作培训教材被广泛使用。
我的小说地图大致如此。尽管十分简单且潦草,却是自己跌跌撞撞一路走来的轨迹。我将沿着这个轨迹,继续跌跌撞撞地走下去,但愿能够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吧!
